-
刘燕舞、魏程琳:一个乡村“精神病”的上访故事
关键字: 上访基层上访神经病人派出所警察涉警上访家庭纠纷【文/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燕舞 魏程琳】
朱莉叶,女,现年70岁,一位执着的上访者。从2004年第一次上访开始,一直持续至今。
在乡村场域的语境中,她是一位地道的“神经病人”。
朱莉叶作为“神经病人”的社会身份,在村落里至少是成立的,尽管到目前止,仍没有权威渠道确定她的“神经病人”的医学身份。
我们在村落中驻村调查近一月,在她所在的村以及附近两个村,我们接触到的人都表示,她是一个“神经病”。以致于我们提出要亲自面对面地与朱莉叶访谈一个上午时,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,他们的眼神似乎在问我们,我们居然找一个“神经病人”访谈,我们的“神经”是否也出了问题?
在和朱的一次访谈中,朱对我们说,她丈夫以及她的三个儿子和儿媳们,也都认为她是个“神经病”,幺儿子和幺儿媳还以替她治风湿病为由将她带到神经医院检查,当她得知是检查神经病时,她笑着讥讽幺儿媳,平时不管她,此时却愿意花钱给她看病,才是真的有神经病。
一、报警及与警察纠纷
朱莉叶进入我们的视野,缘起于2013年7月我们到江南某省江洲乡派出所的一次调查。
所长介绍说,朱莉叶是该所近年来唯一一例涉警上访案例。
在当前的上访研究谱系中,大多均属于涉法涉诉部分的研究,对于涉警上访,关注者相对较少。
2012年4月8日,朱莉叶打电话到江洲乡派出所报警,说是自己的金耳环、金项链和玉手镯被盗。接电话的是警察小王,朱要求派出所所长亲自下来处理。所长说,他正在外面处理案子,实在脱不开身,问朱莉叶能否缓几天。
这并非朱第一次为家里失窃之事报警,从2004年起她就开始给江洲乡派出所不断报案。
因此,朱此前与所长有过多次照面,但对于所长的话,她无法判断出真假,只好作罢,但要求其他警察必须到场。
警察小王和村治保主任一起到朱莉叶家察看了现场,东头的门确实撬坏了,家里的场景似有失窃的可能。
一个星期后,朱莉叶来到派出所,她找到所长问东西是否找到了以及人抓到了没有。所长解释办案有个过程,并戏言,要不请朱把人抓来。
朱则反唇相讥,如果她能抓到人,她要找警察干什么?
半个月后,朱再次来到派出所询问,并十分气愤。她认为派出所办案拖拉,敷衍她。
没有得到理想结果,她就杵在门口不走。
派出所民警老曹问她又来干什么,她不接腔,装作没听见。
老曹就嘟囔了一句“滚”。
朱听了后非常气愤,并质问老曹凭什么要她滚。
她说,这派出所是共产党盖的,不是老曹私人的,她是到共产党的派出所来办事的,不是到老曹私人家里办事,老曹没有权力叫她滚。
朱的质问很有趣,其背后反映了普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,以及要求党的干部为民办事的理直气壮。显然,即使是乡村场域中所“建构”抑或“真实”的一个“神经病人”,也能够善于运用国家的意识形态为自己说话。
因为朱莉叶此前长时间的上访和不断找派出所报案,老曹与派出所的同事其实心里都憋着一股火。朱的质问,让曹一时竟无言以对,便索性粗鲁起来大吼“你给老子滚,你滚不滚?”朱回应说“我硬是不滚”。
曹的粗鲁同样导因于他对朱作为一个“神经病人”的认定。
于是,他的粗鲁加码:“你妈的个X,一个神经病”。
这激怒了朱,她上前与之理论,被曹“推了一下”左肩。
这个在曹眼里的“推了一下”的动作,在朱的说法里是“打了一掌”。
究竟是“推了一下”还是“打了一掌”,定性是很模糊的,而这种模糊的空间为纠纷发生的双方提供了各自的解读理据。
一般来说,上访者之所以上访,大体上总还是“权利”多少受到侵害所致。但并非所有“权利”遭到侵害就会引起上访,两者没有必然关系。即使如朱莉叶这样一个在几乎所有人看来都是“神经病人”的上访者,她之所以发动针对警察的上访,也是在她的“权利”受到警察老曹的“侵害”后,在与整个派出所的互动中发生的。
老曹“推”的时候,所长刚好出来看到,朱莉叶对所长寄予了“厚望”,要求所长证实老曹“打”了她,并要替她“出气”。
让朱的“神经”受到强烈刺激的是,所长说没有看到。
在派出所,这一刻,朱近乎“绝望”。于是,她想到了上访。

处理人民“小事”的乏力与无方最终在互动中逐步将公权力也绑架进来了,图为“上访妈妈”唐慧
二、涉警上访
朱首先到县城的法医鉴定中心做了鉴定,花了400元,但没有验出什么伤情。
朱将法医鉴定结果作为证据。先是带着这份“证据”返回派出所,要求派出所赔偿她到县城的路费和鉴定费。
派出所无人搭理她,于是,她找到乡里,先是找书记,书记要她找分管的副乡长,副乡长要她找主管的综治办主任,综治办主任不断跟她说好话,很亲热地姨妈长姨妈短跟她做工作以安抚她。但在朱看来,好话一箩筐,并没有什么实质作用,不过,她觉得综治办主任的“敷衍技术”让她舒服很多。
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,朱莉叶开始了上访。
上访的诉求很简单,一共三条:一是,要求老曹赔偿她400元法医鉴定费和往返县城的100元路费;二是,要让有关方面都知道有个叫曹XX的警察打了她;三是,有关方面应该对曹进行教育,以帮她出气。
上访的第一站是县公安局。
第一道阻力便是门卫,将她拦在外面,不让她进。
这让她很恼火,她大声质问,这是你门卫个人的公安局吗?这是人民的公安局,你凭什么不让人民进去?她说,她又没有背炸药,她进去是办事,不是要炸公安局。
朱的意志和毅力以及她援引的宏大话语,让她进门成功,但上访仍然未果。
此后持续一个月,她天天往县城和市里跑。
她显然没有再计算她每天跑的路费和误工,甚至问题得不到解决所带来的身心疲惫的成本。因为,这一成本远高于她要的500元。这也说明,她不纯粹是为了钱。“出气”,似乎是挑拨她“神经”的更为重要的考量,而这种“执拗”,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她作为一个“神经病人”的界定,反过来说,“神经病人”的社会身份又更加无助于她的问题得到解决。她的任何真话,在没有铁的证据面前,都很容易被人们当成胡话和笑话。
法医鉴定的结果,让朱莉叶明白一个道理,即她的“维权”仅能从上访这一特殊的行政救济中得到满足,而解决的可能性又取决于她不断地重复上访的坚持程度。
除了县公安局外,朱莉叶陆续到过县信访局,县政府,县检察院,县法院。在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,她又上访到了市检察院,市纪委,市信访局,市人大,市公安局。在市一级的上访,其结果基本上都是让她回县里找相关部门解决问题,而在县里的上访,则基本上都是让她回到乡里解决问题。
然而,正是因为乡里“无法”解决她的问题,她才会到县里和市里上访。
吊诡的是,导因于维稳的“神经”,县乡两级对此均感受到了巨大的“压力”,他们甚至将朱莉叶纳入“特护期”中的重点包保稳控对象之一。
三、家庭纠纷
应该说,涉警上访的发生,是朱莉叶的访中访,既是偶然,也是必然。
朱莉叶说她是个苦命的孤儿。
八个月丧母,十岁丧父,十一岁丧祖母,此后,朱莉叶跟随一个出嫁了的姑妈生活。
或许,童年的缺乏安全感,为其花甲之年后迈向上访之路埋下了种子。
个人安全感的缺乏,有时与对社会安全感的缺乏可能是同步的,寻找一种确定性成为人们克服不安全感的日常生活实践。
朱莉叶在姑妈所在的村子长大,并与该村一民办教师恋爱结婚。刚结婚时,她十分勤劳本分,她丈夫的主要精力是教书,而她基本上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与农活,并生育了三儿一女。
这些后来都构成朱莉叶针对丈夫上访的苦难诉说材料。
步入中年后,村民发现,朱莉叶精神开始间歇性地有问题。
有三个指标,基本反映了朱的不正常状态。一是,在与人争吵后,朱会缠上人家,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中,直到别人见到她就躲起来;二是,她开始偷东西,而且是喜欢偷小东小西,如村民家里的瓜果,集市上的鱼;三是,生活作风上有不检点的嫌疑。
这三个指标,让朱的丈夫如芒刺在背。夫妻俩因此而陷入冷战与热战相结合的漫长过程中。
2003年,朱的丈夫退休,因为早期转成了公办教师,退休后,她丈夫有一笔不少的退休工资,到目前为止,每月约有3000元。
在朱看来,这是一笔不小的钱。
- 原标题:刘燕舞、魏程琳:一个乡村“精神病”的上访故事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。
- 责任编辑:小婷
-
 中国不买美国液化气了,换中东 评论 0
中国不买美国液化气了,换中东 评论 0 把中国货“藏”在加拿大,“我们赌特朗普会认怂” 评论 81
把中国货“藏”在加拿大,“我们赌特朗普会认怂” 评论 81 扛不住了?特朗普释放对华缓和信号 评论 454
扛不住了?特朗普释放对华缓和信号 评论 454 和特朗普一起“孤立中国”?欧盟拒绝 评论 55
和特朗普一起“孤立中国”?欧盟拒绝 评论 55 “美国几代人的亚太布局被毁,盟友终将望向中国” 评论 156最新闻 Hot
“美国几代人的亚太布局被毁,盟友终将望向中国” 评论 156最新闻 Hot-

中国不买美国液化气了,换中东
-

把中国货“藏”在加拿大,“我们赌特朗普会认怂”
-

涉及稀土,马斯克:正与中方协商
-

美国着急放风“即将与日印达成协议”,其实只是…
-

通用电气CEO:别打了,我们还没给中国交付...
-

哥伦比亚总统:我认为特朗普政府把我的签证吊销了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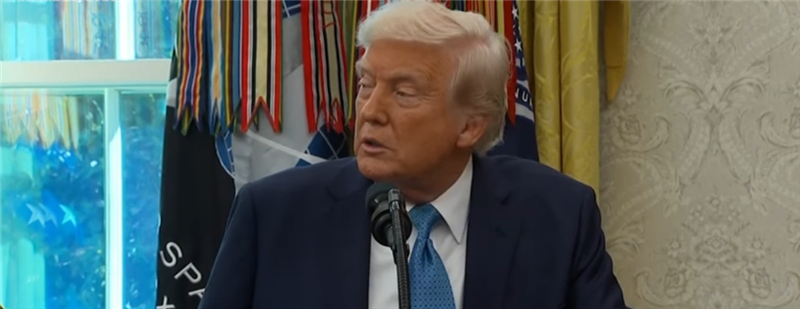
扛不住了?特朗普释放对华缓和信号
-

“孤立中国?东盟不会跟,否则…”
-

“中方对美方鸣枪示警:这回来真的,能一票否决”
-

“特朗普一声令下,美国几十年联越制华努力,白干了”
-

特斯拉净收入锐减71%,马斯克“认怂”
-

普京送给特朗普的肖像画长这样
-

美欧倒逼肯尼亚“转头”,“中国又拿下一局”
-

和特朗普一起“孤立中国”?欧盟拒绝
-

“特朗普把科研领导权让给中国,10年才能恢复过来”
-

鲁比奥要重组美国务院:在大国竞争时代,难以履行使命
-
Copyright © 2014-2024 观察者 All rights reserved。
沪ICP备10213822号-2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:31220170001
网登网视备(沪)02020000041-1号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:沪(2024)0000009
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:(沪)字第03952号
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:沪B2-20210968 违法及不良信息举报电话:021-62376571
![]() 沪公网安备 31010502000027号
沪公网安备 31010502000027号
![]() 中国互联网举报中心
中国互联网举报中心
 上海市互联网违法与不良信息举报中心
上海市互联网违法与不良信息举报中心

 观察员
观察员

